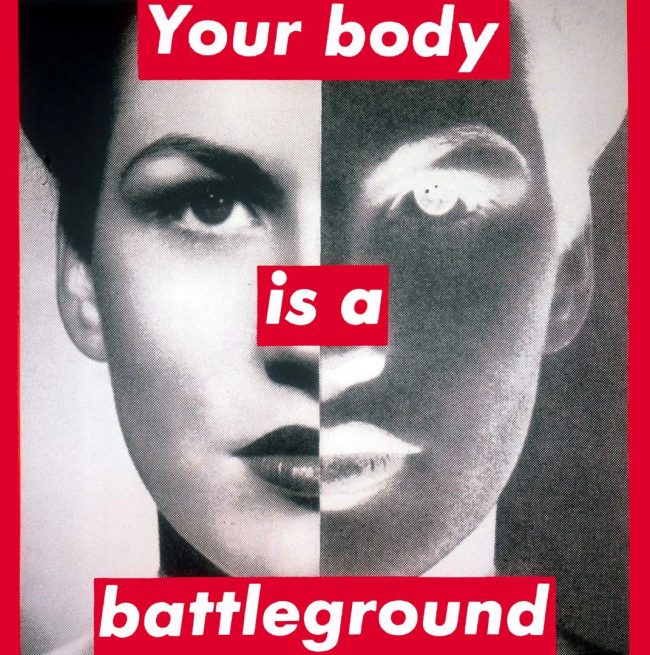WRITERS’ ACQUISITION COMMITTEE (SHANGHAI)
Initiated in September 2021, Longlati Writers’ Acquisition Committee, Shanghai, is formed by four Shanghai-based writers, Jenny Chen, Zian Chen, Suchao Li, Evonne Jiawei Yuan, who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local art scene. It aims to promote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between writers and emerging artists. They will organize monthly visits to gallery and museum exhibitions in Shanghai, conduct research into the works and develop acquisition proposals. Each of them will nominate artists and evaluate each other’s opinions, then make votes to make new additions to the Collection of Longlati Foundation every mo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