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主义: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
国共时期后的毛泽东时代,对于女性身体的西方凝视逐渐退却,但存在着许多新的纷争。这表现为妇女解放运动中萦绕在女性身上的话语,身体既成为表征的修辞手段,又充当着辩论的本体论基础。这些话语大都受生物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影响,强调性的本质差异。即使当时很多人推崇秋瑾式的女英雄人物,鼓励女子“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但二者实则殊途同归,都局限在本质主义的性别框架中。性别的本质主义话语源于西方学者的论述,如蔼理斯(Havelock Ellis)和葛底士(Patrick Geddes)的学说[1]——前者主张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性别动态模型,并相信性行为应该以繁衍优良种族为目的;后者则将性差异还原为血液的差异(男性的血液分解代谢,发散体能;女性的血液合成代谢,储存体能以便于生殖)。虽然这些“科学”论断在如今已站不住脚,但在那个时期却占据了主流位置。它们不仅一致强调性别本质的差异,也强调女性在种族存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最终导致性别本质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发展出女权主义保守国家民族主义与激进国家民族主义两种模式:一方以日本明治政府宣扬的“贤母良妻”为代表,提倡家庭是女性的生活重心,另一方以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为代表,强调妇女应该通过经济独立获得性别平等,重视妇女的生育状况,并将家庭和谐与国家民族的建设联系起来。

《妇女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1915年1月5日在上海创刊,1931年12月停刊。图片:来源于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模式内部也交织着不同的动力。以《妇女杂志》主编胡彬夏为例,学者江勇振为我们指出,当时日本确立的“贤母良妻”范式实际上与其模仿对象(美国)有着很大差距。这在胡彬夏的思想历程中依稀可见:她早年同许多中国女性一样前往东洋留学,并跟随日本教育家下田歌子学习。下田歌子正是当时宣扬“贤母良妻”观念的主导,并力主将妇德与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然而这样的观念在胡彬夏那里发生了反转,旅居美国的经历使她发现这个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词汇无法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也意识到“贤”与“良”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不仅东西方的理解不同,它还随着时间变迁。然而,这其中没有变化的却是其中的男性中心观。这使胡彬夏最终扬弃了这个观念,转而投向美国式的“纯美女性”理型,向既善家务又热心公益的白人中上阶级女性形象靠拢。遗憾的是,胡没有意识到“纯美女性”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脱离男性中心的罗网。

《妇女杂志》主编胡彬夏。图片:来源于网络

日本教育家下田歌子。图片:来源于网络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的话语冲突,可以在对“大跃进”(1958-1960)的不同历史评价中窥见。戈玫(Kimberley Ens Manning)在其文章“向前‘大跃进’?”[2]中,通过口述史重构了毛泽东时期的妇女解放政治。“大跃进”向来被视作近代史上的一个“大灾难”,然而通过重访当时参加“大跃进”的妇联领导,戈玫给出了更多元的解读。首先,作为马克思母性主义原则第一次在现实中的实践,“大跃进”面临着除妇女问题之外的诸多挑战,如后来发生的大规模公社运动和不现实的生产指标。这导致妇女被家庭外劳动与家庭内劳动的需求竞相拉扯。一方面,党和妇联领导意识到女性只有参加家庭之外的生产劳动才能真正摆脱封建的束缚实现性别平等[3];另一方面,党又极为强调母性在家庭中的再生产。周恩来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妇女有着生育和照顾孩子的“天职”。这意味着党既要尽可能实现男女在家庭外劳动的“平等”,又要意识到母性的“特殊性”。其次,左派母性主义存在着对革命与解放的不同理解。戈玫指出,当时的基层党组织仍然秉持着革命时期毛泽东式的斗争和牺牲思想,这要求一种身心关系,即妇女需要也可以用意志战胜身体的客观限制。正是这样的观念,导致当时妇联领导漠视母性的“特殊性”,认为妇女只需作出更大牺牲,便能实现党对妇女解放的期望。对女性家庭内外劳动需求与解放的不同诠释,导致“大跃进”对不同当事人留下了迥异的历史记忆。如前江苏妇联主席石坚认为,如官方历史所描绘的,马克思母性主义在“大跃进”期间处于“受围困”的窘境。但对另一些基层领导而言,“大跃进”是妇女解放最伟大的时期,妇女主体及其能动性得到切实的重塑,其成就多过损失。

1958年,妇女炼铁厂。图片:来源于网络

1958年,妇女大炼钢铁。图片:来源于网络
“东方尤物”的身体书写与被放逐
1949年后,毛泽东式的乡村平民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优先于城市意识,直到80年代晚期,“城市”才成为现代性转变的核心话语,其时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4]。当城市意识逐渐崭露头角,现代化都市(如上海)才在文学想象中开始扮演显要的角色,现代化都市女性的身体写作也从这时开始兴盛,其中尤为独特的例子当属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们试图将这位20世纪末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与20世纪初的两位“新感觉派”领袖刘呐鸥与穆时英笔下的女性身体并置,理解其中现代性、女性身体与社会性别政治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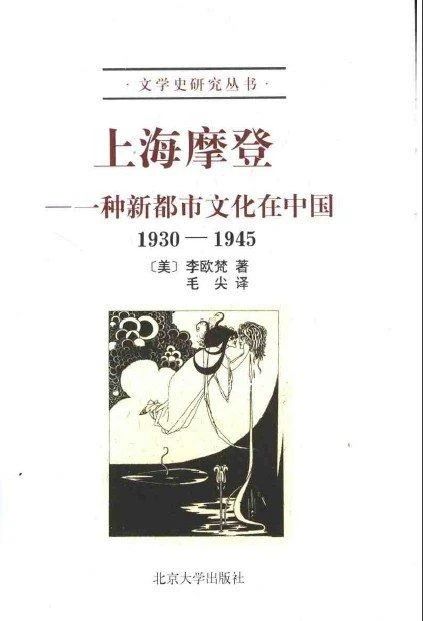
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上海摩登》中,李欧梵细致地分析了刘穆二人作品中的女性身体肖像。他指出,刘呐鸥的女性形象多遵循一种奇怪的性压抑“理论”,她们大胆直接,却又抑制着自己的欲望。作为第一个拥抱好莱坞女星形象并将她们带入都市小说背景的现代中国作家,刘呐鸥提供了一种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男性观看“她们”的方式,从而呈现了一种与西方男性凝视颇为不同的凝视结构。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其电影理论中提到:“观看快感被二分为主动/男性与被动/女性,男性凝视将其幻想投射在女性身体上,使后者被相应地风格化。”[5]而李欧梵认为,刘呐鸥小说世界中的凝视结构是相反的,男性在其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女性则扮演着一个异域的理想人物。之所以如此,是源于文化交叉产生的相互异域化过程。以法国作家兼外交家保尔·穆杭(Paul Morand)为例,他的作品渗透着明显的东方主义,普遍将异域的东方女性幻想为“亚人类他者”。而作为将穆杭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刘呐鸥不仅意识到穆杭小说中的殖民意味,也在自己的作品中镜像了这样的幻想。在这里,二人小说中的“异域”女性成了一面双面镜,既呈现着西方对东方女性的幻想(穆杭),又映射出东方对西方女性的幻想(刘呐鸥)。只是,当异域想象被镜像的同时,性别凝视的不对称结构却遭到了翻转。因为性别在二人的描述中总是带着地域(东西方)的符码,所以刘小说中的性别凝视的不对称结构,也暗示了中国与西方在相互异域化过程中的不对称。其小说的情欲结构揭示了中国在现代化与半殖民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女性(他者/西方)虽是欲望与角逐的客体,却占据了故事的绝对“主体”。这也解释了穆时英小说中呈现的“尤物”形象——“一个散发着某种无边际不安的,预示着认识论创伤的人物……她所携带的威胁不是完全易辩的、可预见的或可把握的”[6]——这些恰恰是他们对西方/他者的无意识写照。

卫慧,《上海宝贝》。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了20世纪末,卫慧的《上海宝贝》成为了一个“尤物”进行自我身体书写的案例。《上海宝贝》于1999年出版后引发了不同的回应和论辩,并最终被官方列为禁书。它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大量对女性性欲的第一人称书写,还在于故事人物的奇特设置——一个年轻女主人公倪可(Coco)与一个阳痿的中国男朋友以及另一个男人味十足的德国情人。一些西方学者将卫慧大胆的身体书写与“身体女权主义”(corporeal feminism)联系起来。因此有人认为《上海宝贝》或许是一个发现“女性本质”的写作实践。然而钟雪萍指出:《上海宝贝》一类的文学作品可能利用了“身体写作”在中文世界的诱惑性,且美女作家的名头往往以性别歧视或是厌女的方式被人认知。这让原本意图解放女性的身体书写,加剧了女性特质与性欲的本质主义刻板印象[7]。
另一方面,《上海宝贝》中对当代城市图景和文化主题的拼贴,实则与刘穆二人的异域化城市图景大体无差。如果将卫慧的人物设置与刘穆的小说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倪可丰富的社交与性经历活脱脱像刘小说中“未曾跟一个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的女性[8]。而《上海宝贝》中势弱的中国男性也恰似刘穆笔下惶然面对“尤物”的男主人公。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在卫慧的书写中,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实现解放的女性倪可,成为了一面能够自我陈述的“异域”双面镜,赤裸裸地照射出了现实——在亚洲女性的眼中,东西方不对称的凝视结构呈现了重合,也演化为《上海宝贝》中中国男人与西方男人的对立。这样看来,卫慧的小说并不如钟雪萍在其文章中判定的全无“历史感”,事实上,它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产物。在其中,“他者性”作为某种“旁观者清”的“话语” 揭示了一个难堪的局面[9]。这对于当时正在进行市场改革与急于建立新(男性)主体的中国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上海宝贝》遭禁,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父权作出了双重否定——这否定既来自西方,又来自女性;更是因为,女性在其中作为双重意义上的他者,竟以第一人称视角观看了双重否定带来的受挫。我们可以说,官方通过禁止这样的书写,试图逃脱的是他者制造的梦魇,并希望借此跨过历史创伤重建主体,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女性的身体书写也被短暂地划上了句点。

Judy Chicago, What if Woman Ruled the World,2002
Courtesy of the Long March Project
离《上海宝贝》遭禁仅隔三年,泸沽湖计划《假如女性统治世界?》(What if Woman Ruled the World?)”由“女性主义艺术的开山鼻祖”朱迪·芝加哥发起,与长征计划的策展人邱志杰、卢杰组成策展团队,在“世界最后一个母系氏族部落”中展示了十几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细看长征计划的沿途战报[10],我们会发现其中分布着许多因“文化转向”产生的裂缝:其一,在7月25日朱迪与长征的策展会议中,朱迪一开始与中国女艺术家见面,对作品方案中“涌动的非艺术的因素”感到压力,而在当晚与两位男性策展人沟通后才“感到靠谱”。这一细节暗示了朱迪这位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导师对“非艺术”的忧虑。然而,我们无从知道她何以掌握着非艺术的评判标准,且这种忧虑如何可以由两位男性策展人驱散。在这里,策展人扮演的是(东方与西方或“非艺术”与“艺术”的)中介角色吗?还是如前述的大多女性主义男性知识分子一样,成为西方“进步式”(当代艺术)理念的附随?其二,在7月27日,卢杰和朱迪在湖边散步时萌发了在泸沽湖打造《女性之家》(Womanhouse)想法,这一想法在当日会议中被接受,却在第二天被艺术家们推翻。《女性之家》实为朱迪与米莉亚姆·夏皮罗(Miriam Schapiro)以及她们的学生,于1972年在好莱坞的一座废弃建筑中实施的空间装置。朱迪不仅希望将《女性之家》移置到泸沽湖的奇地山庄,更是沿袭了她之前与学生的交流方式——大家一起围坐成圈,营造一种“圆形,如子宫般”的空间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二人的学生在当时曾公开表示过对此“子宫氛围”的不满,并揭露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权力悬殊。我们很难揣摩朱迪将此作品及其实施方式在泸沽湖复现的潜在意图,但中国女艺术家们似乎是意识到了这其中的权力失衡,才最终拒绝了朱迪声称的“奉献”。最后,沿途战报清晰刻画了朱迪对摩梭族文化的想象转变。泸沽湖作为摩梭族人的栖息地,对这位俄裔犹太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个绝对的异域。我们很难辨明她对泸沽湖的想象是否残留着东方主义元素。然而当她后来与摩梭族人交流后发现,原来摩梭族的女人更苦更累,并且她们并不希望保持这种部落状态,而是渴望早日跟上现代化进程,朱迪的想象因此受挫。上述三次受挫,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身处异域的西方白人女性身体的肖像,朱迪的身体,作为整个计划的焦点,被一次次受挫搅扰,最终表征为身体的水土不服(朱迪的高原反应)。

The front page of the exhibition catalog for “Womanhouse” (January 30 – February 28, 1972), feminist art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Judy Chicago and Miriam Schapiro, co-founders of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CalArts) Feminist Art Program.

Judy Chicago addresses a gathering of volunteers in the Dinner Party studio, ca. 1978. Photograph by Amy Meadow. Judy Chicago Visual Archive, Betty Boyd Dettre Library &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
“假如女性统治世界?”原本提供了一种权力结构的想象,希冀借摩梭族这个被神话了的母系社会获得某种超自然力(就像朱迪想借超自然力解救自己昏厥的丈夫一样),作出强有力的发问。但最终,文化交叉产生的复杂情境以其自身的厚度映衬出了个体想象的单薄,也导致朱迪的必然受挫,使她的发问变成了(身体)虚弱的探问。这个问句中的“女性”多大程度上局限于白人中产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她能否容纳摩梭族女性的视角,“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结构真的是可以或值得追寻的吗?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将揭示早期女性主义对身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11]的忽视。这一理论框架试图理解相互交织和重叠的社会身份,并指出,如此复杂的身份可能让个体既被赋权又被压迫。这恰恰解释了上述现代化进程中萦绕着身体的诸多战争,同时也预示着(福柯意义上的)战争将永无止尽。
文/陈嘉莹
注释
[1]江勇振.“女性、母性与生物界通律:《妇女杂志》的前半期(1915-1925)”. 王政、高彦颐主编.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58-97.《妇女杂志》是1915年至1931在上海发行的一份杂志,是20世纪前半段中国主流的妇女杂志。
[2]王政、高彦颐主编.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129-155.
[3]大跃进”时期采用了公共食堂和集体托儿所。这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构想相符,如李达就指出要让女性从贤妻良母的角色中走出来需要新的方案——“一个叫做儿童公育,一个叫做会食 ”。
[4]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2.
[5]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19.
[6]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1.
[7]王政、高彦颐主编.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25-226.
[8]刘呐鸥.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见《都市风景线》.
[9]王政、高彦颐主编.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24.
[10]http://longmarchproject.com/zh/s6report-lugu/
[11]交叉性是一个理论框架,用于理解由多个个人身份的组合所引起的特殊歧视和压迫,例如性别、种姓、性、种族、阶级、宗教、残疾、外貌,以及身高。交叉性可用于识别人们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组合而经历的优缺点。






